这是半个多世纪以前的事了,我们的祖国正遭受日寇的侵略,前线将士浴血奋战,半壁河山沦陷了。同胞们颠沛流离,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。我们家也从苏州逃难到云南。父亲到云南大理办了一所学校,我们家就在大理住下来了。从1937年离开苏州至1938年到达云南昆明,经过上海、江西庐山、湖南湘潭、桂林、出友谊关(那时叫镇南关)经越南到昆明,一路上走走停停,我们孩子们的学习受到很大影响,只在庐山从南昌搬来的葆灵女学上了几个月学,又在昆明的昆华女子中学念了半年书,拿到了初中毕业文凭。我们是1939年初到达大理的。我本应该上高中的,但是父亲办的中学不收女生。大理有一个女子师范学校,那个学校水平太差,教的东西我都学过了,因为苏州的学校水平较高。父母决定让我在家自学,由父亲教我中文,母亲教英文,请一位数学老师教我数学。母亲教英文很认真,可是父亲太忙,没有多少时间教我。那位数学老师也是从江浙一带逃难来的,他教我几何和三角,教得很好。另外,母亲还教我世界历史,她在美国就是学历史的,所以很熟,就像讲故事一样讲给我们听。这样在家学了半年。听说有一个大学搬到喜洲,叫武昌华中大学,是一个教会学校,正在招生,喜洲离大理四十里路,不太远。父母说让我去考考看吧!我没有高中毕业文凭,据说可以同等学历资格去考,我们就去报了名。我那时还不满17周岁,还是一个孩子。记得考试时是母亲陪我去的,前一天,我们就乘了滑竿从大理城走了40里路到喜洲镇,在朋友家住了一夜,第二天到学校考试。我一点都不紧张,本来就是去试试看的,能否考取无所谓。只考三门,中文、英文和数学。中文、英文各要求做一篇作文,和一些问答题。我觉得都不难,因为在家,每星期都要做中、英文作文一篇,由父母修改。数学题有代数、几何和三角,也不太难,大部分都会做,考完了感到很轻松愉快。那个夏天还学会了骑马,因为那时云南交通不便,人们多骑马代步。有一天收到华中大学的一封信,原来是我的录取通知书,大家都非常高兴。到九月份开学我就成了一个大学生了。

(华中大学在喜洲时的教师合影)
大理是一个非常美丽的城市,在苍山洱海之间,是狭长的一条地,南起下关,北至上关,是洱海的两端。下关和上关之间有大理城和喜洲镇。有下关风、上关花、苍山雪、洱海月之说法。大理古时为南诏国都,喜洲因蝴蝶泉而闻名。喜洲有一个姓严的盐商,在外面赚了很多钱,回家乡盖了许多房子,还建了医院、图书馆和一所中学。华中大学迁滇,到昆明找校址,正好遇到严家的人,说“你们就搬到我们喜洲去吧!”后来华中大学就搬到了喜洲。学校所在地原是一座庙,把大殿改为礼堂,把两旁的厢房改建为两座小楼,作为教室、实验室、图书室、办公室等等。有一个操场,一个校园,校园旁还有一些平房。校园里有参天古树,还种了许多花木。学校离镇约两里,教职员和学生都在镇上租用民房作为宿舍。因为是从湖北搬来的,老师和学生大多讲湖北话。校长是德高望重的韦卓民先生,他在基督教界颇有威望,而校务多由洋人掌权,教务主任、财务、会计等都是洋人,因为那是一所教会学校,由美国一个教会来办的。教授们大多是很有学问的人,有留学博士,有国内知名人士。也有外国人。学生只有两三百人,高年级学生都是随学校从武昌搬来的,一年级新生有的是从湖北和湖南招来的,也有在昆明和大理招的。
我是学校里最小的学生,年龄小,个子也小,大家都叫我小伢儿。记得一年级我选了生物、化学、英文、微积分、还有中文。教生物的陈伯康先生和教化学的张先生都是留美博士。生物学我念得最好,经常考一百分,因为要背的东西较多,我都背得很熟。上课时老师提问,那些大的学生答不出来,我就偷偷地笑,老帅说:“那个小伢儿在笑,她一定会了,叫她来答。”我全答对了。教微积分的是一个外国人,他管财务也教数学。他教得一点也不好,学生都听不明白。教英文的是一个德国女教师,她教得也不太好,其实英文系里有很好的老师,大概因为这个德国人不会别的,叫她来对付一年级的外系学生。教中文的是游国恩先生,他是一位很有名的教授,他讲课很生动,引人入胜。他教我们用文言文作文,他改文章很认真,我经常得到他的好评,所以很喜欢上他的课。政治是必修课,国民党派一个教官来教三民主义,大家都很讨厌那个教官,上课也都马马虎虎,考及格就行了。
女生宿舍是一个四合院的民房,8个人一间房,四张上下铺的床,中间放几张小书桌。记得同房间的有汪海珍、董一男、张葆英、张爱贞、张保贞、丁宝筠等人,大家相处得很好,尤其因为汪海珍、董一男、张保贞、和张葆英都是生物系的,在一起上课,关系更加密切,我比她们小几岁,她们都叫我小伢儿。有一天,天气很冷,刮大风,我们的房门被风吹开了,大家都怕冷,把被子拉紧,不愿起来关门,我睡在上铺跳下来把门关好了。她们就给我起了一个外号叫做:“勇敢的小兵”。男、女生在各自的宿舍里办伙食。抗战时期政府发给沦陷区学生贷金,我们就拿这笔钱包伙。我们宿舍约有四、五十个女生,请了一个厨师,每天有一个学生轮流监厨,由那个学生和厨师一起去买菜。如果餐桌上有土豆准是广东人买菜,如有辣椒准是湖南人买菜,如菜做得很甜,准是上海人监厨,为这事大家经常哈哈大笑。因为钱少,伙食不好,每星期只有一两次加餐,有红烧肉等。有时家里给了钱就到街上买点肉,腌起来挂在床头,再买点鸡蛋,做蛋炒饭佐餐。镇边上有一个老太婆,她煮了牛奶鸡蛋卖给学生,她也可代学生炖鸡,草屋里放上几只桌椅,学生们就在那里吃。我有时也和几个同学到那里去饱餐一顿。从学校到镇上的宿舍,走的是乡间小路,两旁都是稻田,到了傍晚你可以看见学生们三三两两在田间散步,夕阳西下,映着远处的苍山、洱海,鸡犬相闻,真好像置身于世外桃源。
学校里没有电灯,起先晚上在礼堂里点一个大气灯,学生可到那里自习。后来物理系的教授用卡车发动机发电,各实验楼里都装上了电灯。可是宿舍里没有电灯,每人点一盏菜油灯,功课多或要考试的时候,只好在油灯下挑灯夜读。
我家在大理,星期六吃过午饭,我就走路回家,要走四个小时,傍晚才能到家。只能住一晚,第二天即星期天下午又要走回学校。后来知道可以租马来骑,但是比较贵不能经常骑马,还是走路的时间多。我常常请同学到我家去玩,妈妈做了许多菜招待他们。和同学们一起走路或骑马,一路说说笑笑也不觉得累。
在我大学二年级的时候,因为大理的盐里缺碘,妹妹和弟弟年纪小,甲状腺开始肿胀,而且外婆在上海生病,母亲决定带弟弟、妹妹到上海去,父亲和我留在大理。他们是经越南海防到香港然后到上海的,本想去一段时间就回来的,但是正好遇到珍珠港事件,太平洋战争爆发,他们就回不来了,我们家分居两地。父亲本来有胃病,母亲走了,他的饮食无人照顾得了胃溃疡大出血。幸亏有一位江苏来的钟医生及时给他治疗,才得以脱险。我在学校得知他生病的消息,赶紧连夜走回家。一个人走黑路,因为心里着急,倒也不觉得害怕。
走时太急来不及请假,教务主任是个洋人,他很生气,说我不请假不守纪律,晚上一个人出去,要以开除处分。后来还是校长替我说情,才免于处分。记得那天我到大理正好遇见韦宝谔,他是校长的儿子,一定是他跟校长讲的。那个洋人教务长叫什么名字记不得了,因为他的脸很红,他对学生很凶,大家叫他红罗卜头。
父亲病了没人照顾,我只好请假在家侍侯,请了两个月假,父亲才慢慢好起来。我回到学校,功课赶不上,很辛苦。校长对我说我年纪太小,以后毕业出去工作也不方便,不如慢慢念,在校多念一年,把基础打好。开始我在化学系,因为母亲希望我学医。但是我的生物学念得好,老师也喜欢我,而我的数学念得不好,因此生物系的老师劝我转到生物系。我退掉了有机化学和物理两门课,留待明年再念,我感到轻松多了。多念一年很有好处,我可以有时间选修中国文学,和英国文学。这些课都是有学问的老师教的。还选修了中国历史和经济学等课。哲学在华中大学是必修课,由韦校长亲自教,他用英文讲课,我觉得很玄妙。
课外我还参加英文系同学演戏,我演一个小孩子,挺有意思的。
生物系有四、五个老师,除陈教授外,还有吴醒夫老师、陈培生老师等,后来陈伯康教授走了,来了一位萧之的教授,他是哈佛大学博士,他的太太是美籍犹太人。学生很少,最多时也不过七、八人。老师们教课都很严格认真,尤其是吴、陈两位年轻老师,还有化学系的两位讲师,都是饱学而认真教学的老师。我的解剖学、发生学、组织学、遗传学、分析化学、有机化学等课都是跟他们学的。到了四年级,生物系只有我一个学生。虽然只有一个学生,老师还是照样上课。我的毕业论文是萧教授带的,做的是云南各民族血型的比较。到 各地取各个少数民族的血样,东到呈贡、西到丽江去了许多地方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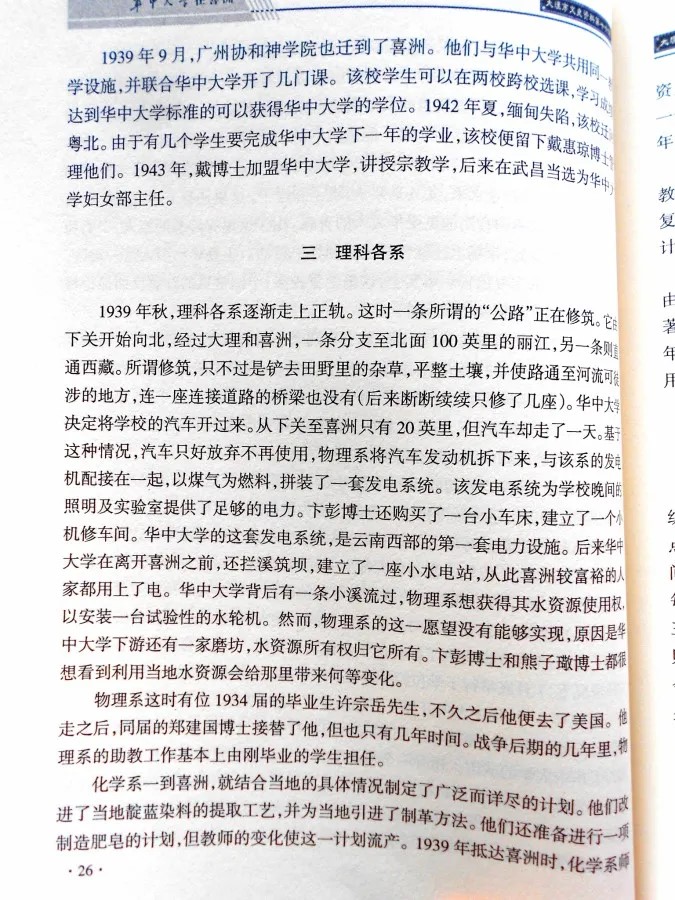
(节选自《华中大学在喜洲》)
我们是1943年的春节到丽江去的,一行四、五个人,有萧先生、萧太太、我、还有两个同学,其中有一个是劍川人,他做我们的向导。我们是骑马去的,从喜洲到丽江走了五天。一路上朝行夜宿,晚上睡在马店里。人和马都住在一起,一个房间拴马,隔壁一间铺上几个草垫,各人把带来的被褥铺在草垫上就是床了。因为走累了也睡得很香。店主人把马喂饱了,弄点饭菜给我们吃。记得饭和鸡肉都特别硬,咬不动,可是没有别的东西可吃,只好胡乱吃一点。经过邓川、洱源、剑川,这一带是白族聚居地,白族妇女爱唱歌,一路上看到那里的风土人情,听着美妙的歌声,很有意思。到了剑川,住在那位同学家里,他们家的房子很大是当地财主。主人做了许多好菜招待我们,晚上月明天清,主客谈笑风生,一扫多日的疲劳。快到丽江就看见玉龙雪山了,白雪皑皑的山顶覆盖着浓绿的山,满山遍野的杜鹃花,鲜艳夺目,美不胜收,我们好像到了仙境一般。即使是一路抱怨的萧太太也驚叹如此美境不虚此行了。
丽江是一个古老的城,街道、房屋很有特色。这里是纳西族聚居的地方。他们是妇女当家,只见满街做买卖的、干活的都是妇女,连赶马帮的也是妇女,不知男人到哪儿去了,也许在家带孩子吧!萧先生带我去找到了洛克博士(Dr. Rock),他是美国人在云南西部多年,为美国国家地理杂志写文章很有名气,当时住在丽江雪松村。他住在一个木屋里,摆设很简朴,门前有一条大狗,很凶。主人出来叫住,我们才得进屋。经洛克博士的帮助,我们调查了雪山南和雪山北两个村的居民的血型。这些村民曾受惠于洛克博士,和我门合作得很好。经统计总结,山北那个村的居民血型比例指数和青海的数据相近,而山南则和白族相近。这与洛克博士从人文科学调查的结论,认为丽江北边居民是从青海迁移来的论点是吻合的。通过做论文,萧教授教我如何查资料、做试验、实地调查、数据分析、写总结等,学到许多东西。
学校里有许多基督教教徒,礼拜天要做礼拜,就在原来的大殿里,把佛像用布遮盖起来。我喜欢听他们唱歌,有时也去做礼拜,但是不信教。过圣诞节很好玩,他们表演耶稣诞生的故事,还唱圣诞节的歌,我也学会了一些歌。
有一次镇上流行霍乱,病死了很多人,街上哭声震天,非常悲惨。这是我在喜洲遇到的最可怕的一幕。幸亏我们学校的人因为讲卫生没人得病。校医教会学生打预防针,我们都到镇上和附近村里去给人打预防针。
在华中大学和我交往较多的在一年级是熊爱莲,她和我一起念的课较多,她是物理系熊教授的女儿,她的学习成绩很好。我们常和同学们一起去骑马、爬山,有时许多同学一起到洱海去划船。二年级的时候来了黄小玲,我们常在一起学习和玩耍。常和我们一起出去玩的男同学有冯容保、宋文麟和韦宝谔。父亲辞去大理师范学校校长之职,搬到喜洲来休养,我住在家里很舒服。父亲对我很严格,不许随便交男朋友,有几个男同学找过我,父亲不同意我和他们交往,我也无所谓,也就作罢。后来父亲到昆明西南联大任教,1943年母亲和弟弟经过种种惊险和困难,从上海回到昆明,我在那年暑假也到昆明和他们团聚。1944年夏天我从大学毕业了,记得在毕业典礼上我代表毕业班同学讲了话。我就依依不舍地离开了我的母校华中大学,离开了风景优美的喜洲和大理。

(华中大学西迁办学纪念碑)